大国技术与全球化(二)为什么基础科学的研究只能由国家主导而不是交给市场?
斯密定理简洁明了地告诉我们,国家和企业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化才有可能获取最顶级的技术,而融入全球化需要突破政治市场和思想市场。

不过,斯密对技术引致规模递增的认识是不完整的。
自由市场促进专业分工,专业分工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引发规模递增,规模递增进而导致垄断。简化逻辑即是自由市场导致垄断,斯密担心逻辑上无法自洽,故中断规模递增方向上的研究。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概括了斯密这一担心,被称为“马歇尔悖论”。
此后百余年,经济学家在此方面毫无建树,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进入了边际递减的数学研究领域。直到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在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科学与统计学分部主席一职时发表了一篇演说——《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这篇演说沿着斯密定理往前走了一步。
杨格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2】。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什么意思?
杨格其实使用了萨伊学说,即有效供给创造有效需求,认为专业分工可以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供给,进而开拓有效需求,拓展市场规模。杨格指出:“某一产业的增长率是以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为条件的。”这其实是萨伊定律的另一种表述。杨格认为,“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
在经济学历史上,杨格这篇文章价值非常之大,杨格自己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然而,这篇文章被埋没了50年之久,无人问津。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感到奇怪:“令人不解的是在杨格精辟的文章之后,经济学界尽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
我们沿着杨格的方向往前看。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全球化产业分工越来越精细,技术供给端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基础科学决定了一国乃至全球技术的高度。在斯密时代,技术受市场规模制约,技术创新具有相当的适应性、自发性,同时技术创新多为贴近市场的应用型技术。英国科学家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打开了近代科学的大门。但是,当时的基础科学距离市场还比较远。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工程师与应用技术推动的,瓦特的祖父和叔父是机械工匠,其父亲是木匠,瓦特是机械工程师,改良了蒸汽机。
到了杨格时代,进入买方市场,回归到萨伊学说,技术创新从适应自发转向主动拓展——新技术创造新产品,新产品创造新需求。二战后,基础科学与市场的距离大大缩短,国家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对新技术、新产品与新市场的影响巨大。
但是,基础科学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外部性。
外部性是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提出来的概念【3】。所谓外部性就是溢出效应,基础科学是一种信息,信息容易被传播和习得,成为类公共产品。如杨振宁的杨-米尔斯(Yang-Mills)理论,是全人类共享的成果,其贡献是全人类的。
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使用外部性原理提出了最有效率等式。按照庇古的理论,科学家提出的原创性基础理论被广泛传播与应用,即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这说明社会占了私人的便宜【4】。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私人企业不愿意投资基础科学,科学家也不愿意搞基础研究。所以,外部性导致基础科学成为低效率、无效率的市场。
这该怎么办?
既然市场无效,企业不投资,那只能政府来投资。早在1945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的万尼瓦尔·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著名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阐述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报告建议成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负责资助基础科学研究。根据这份报告,美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混合模式:即联邦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和非盈利科研机构四类主体有效分工协作——避免基础科学的公共特性问题。
外部性也会导致政府投资受损,为什么国家愿意投资基础科学?
马歇尔是这样解释的,他分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内部经济激励企业投资技术,实现规模递增,进而获取垄断利润;外部经济削弱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但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因为外部经济提高了其他人的收益。这就是马歇尔悖论。他试图通过整体效率不受损来化解斯密的担忧。
政府愿意投资基础科学,外部性让政府投资受损,但整个国家均受益。技术增长理论开创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支持马歇尔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外溢不影响帕累托改善。所以,根据萨伊学说和“斯密-杨格定理”,国家投资基础科学,避免外部性问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
但是,罗默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技术外溢却影响着国家力量之此消彼长、兴衰更替。
在全球化时代,技术外溢到国际市场,被他国免费获取,会导致政府投资受损,进而打击国家投资基础科学的积极性。基础科学,投资巨大,周期很长,风险不可控,但是收益均沾,哪个国家都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
不过,在全球化时代,有两类主体还愿意投资基础科学:一是大型跨国公司;二是全球化国家。
这个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解释。外部性导致利益均沾,出现搭便车现象,该怎么办?奥尔森认为创造两个条件集体行动可以持续: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这两个条件让组织者获得超额收益(超过集体的平均收益),推动集体行动前进【5】。这可以概括为“奥尔森效率”。
在全球化时代,大型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国家投资基础科学的外部性损失相对较小、收益相对较大。对于整个国际市场来说,外部性不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效率。基础科学越发达,经济全球化的效率也就越高,而依赖于全球化生存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国家的收益越大。
比如,Java最初是由Sun Microsystems开发和支持的,该公司后被甲骨文收购。C语言是由美国电话电报的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丹尼斯·麦卡利斯泰尔·里奇发明的。他还与肯·汤普森开发了大名鼎鼎的UNIX操作系统。
美国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大学与科学家研究基础科学。美国国会在1980年代通过的《拜杜法案》规定,允许大学和其他非盈利组织获得政府资助项目的发明专利。这个法令促进了技术成果转化。谷歌公司最初的PageRank算法,就是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字图书馆计划(DLI)资助的项目。还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拉里·佩奇用这一算法创立了谷歌公司。
可见,编程语言的开发,让全世界受益,而大型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国家获益也是最大的。奥尔森效率促使大型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国家愿意投资基础科学,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全球最顶级的技术。
相关阅读
-

一直以来,人们就对于大海有着一种神秘的向往,大海深处有什么呢?神秘的海洋究竟还有着多少的未知生物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呢?..._新浪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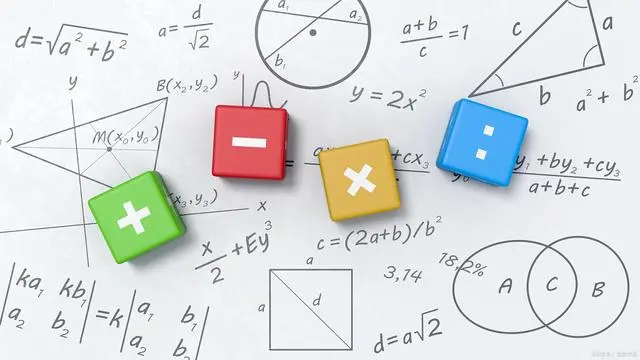
初中数学怎样学好?由于初中孩子的数学基础不同,所以导致很多学生对这个科目的看法也不同。有的学生基础好,学习数学不那么吃力,就会觉得这个科目难度不大,但有的初中生数学基础差...
-

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也都是比较大的,可能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并不满意,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在下班或者周末的时间去做兼职。在手机上接单的兼职就会更加的方便了...
-

如果再往下300米,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凶猛的鲨鱼,叫做欧氏尖吻鲨,它最大特点便是其嘴和上颚是分开的,所以它是张嘴吃东西的,由于视觉能力很差,只能靠嗅觉和触觉进行导航,另外...
-

一直以来,人们就对于大海有着一种神秘的向往,大海深处有什么呢?神秘的海洋究竟还有着多少的未知生物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呢?..._新浪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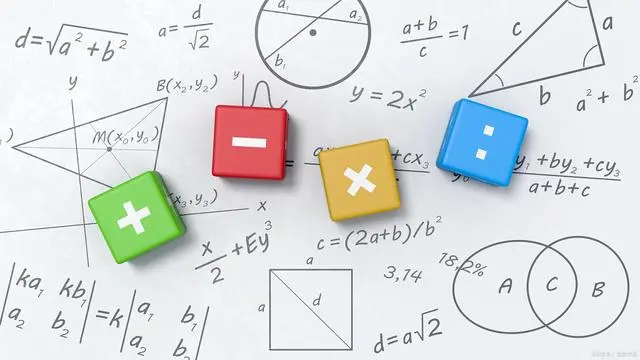
初中数学怎样学好?由于初中孩子的数学基础不同,所以导致很多学生对这个科目的看法也不同。有的学生基础好,学习数学不那么吃力,就会觉得这个科目难度不大,但有的初中生数学基础差...
-

如果再往下300米,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凶猛的鲨鱼,叫做欧氏尖吻鲨,它最大特点便是其嘴和上颚是分开的,所以它是张嘴吃东西的,由于视觉能力很差,只能靠嗅觉和触觉进行导航,另外...
-

重读张颖清!全息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从一只苹果吃出了中医所有理论!...
-
心理学上有个“情绪ABC理论”,A代表事情的起因,C代表事情的结果,B代表对A的认知和情绪。由于每个人针对A会产生不同的B,从而导致正面或负面等不同的C。改变B...
-

60多项中国第一,400家机构重仓,社保基金抢筹,全球龙头被严重低估!
你相信光吗?知道光的力量有多大吗?激光,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大到飞机、轮船,小到厨卫、电器,激光作为先进的加工利器被广泛运用于装备制造领域的方方面面。...
发表评论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